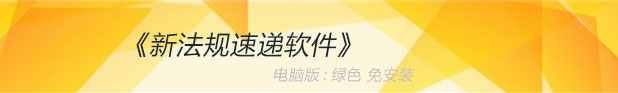[ 楊海峰 ]——(2005-3-27) / 已閱18626次
論我國刑事訴訟法對無罪推定原則的吸收
一、思想的變革
我國刑事訴訟法律觀的產(chǎn)生、形成和發(fā)展,具有深刻的中國歷史背景和文化背景根源。幾千年的儒、法兩家刑事法律觀,深深地影響著我國刑事訴訟法的制訂和執(zhí)行,我國社會所經(jīng)歷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產(chǎn)品經(jīng)濟、有計劃的商品經(jīng)濟和社會主義的市場經(jīng)濟等不同的經(jīng)濟體制所產(chǎn)生的意識形態(tài),也影響著訴訟法律觀,因為一定的刑事訴訟的法律觀必然反映著一定的經(jīng)濟形態(tài)。這正是我國步入依法治國的軌道以后,人們感到步履維艱的原因。刑訊逼供、久押不決、超期羈押、辯護律師參與訴訟難、證人作證、出庭難等等問題仍然困繞著我們。經(jīng)過幾年來的實踐,已經(jīng)充分地證明,一項先進的司法制度的貫徹實施,首先遇到的一個問題,就是訴訟法律觀的轉(zhuǎn)變問題,這種轉(zhuǎn)變要經(jīng)過一個漫長的痛苦的磨合期,要有一個認識的過程、實踐的過程,要有一個從不自覺走向自覺的發(fā)展過程。
對刑事訴訟法本質(zhì)的認識,長期以來,特別是從5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由于受前蘇聯(lián)式的制度結(jié)構(gòu)和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把法律僅僅當作是把持國家政權(quán)的統(tǒng)治階級的意志。在這種國家主義法律觀的指導和統(tǒng)治下,作為比較敏感的刑事訴訟法,從立法到執(zhí)法,無不以國家本位為主宰。在“以階級斗爭為綱”時期,把刑事訴訟法定位于“打擊敵人”、“鎮(zhèn)壓反革命”的工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被提到議事日程。但是,由于我國傳統(tǒng)法律文化中缺少個人的自主地位和獨立價值,國家本位的價值觀根深蒂固。在刑事訴訟領域里,特別是在執(zhí)法的環(huán)節(jié)中,重國家輕個人,重打擊輕保護,重控告輕辯護,重實體輕程序等等,其明顯的價值取向就是國家本位。無罪推定原則是否適用于我國刑事訴訟法的問題,以往一直是作為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傾向、精神污染加以批判的,但是,隨著我國法治化進程,無罪推定原則最終登上了中國刑事訴訟的舞臺。
二、無罪推定原則的吸收
無罪推定是西方國家在否定中世紀糾問式訴訟制度的基礎上形成并發(fā)展起來的一項刑事訴訟法原則。它與刑法上的“罪刑法定”的原則相配合,成為西方國家刑事法律的基礎。無罪推定在法律中的確立始于法國1789年頒布的《人權(quán)宣言》。《人權(quán)宣言》第9條規(guī)定,“任何人在被宣判為犯罪者之前,均應假定為無罪。”此后,這一原則又在許多國家憲法或法律中得到確立。由于歷史的原因,長期以來,我國法律界不少人對無罪推定原則存有一些偏見和誤解,致使這一原則未能在我國學術(shù)界和法律中得到肯定。但近年來我國立法機關通過的法律以及司法機關發(fā)布的帶有司法解釋性質(zhì)的法律文件也吸收了這一原則的部分內(nèi)容。在從1993年開始的刑事訴訟法修改過程中,許多學者和專家均提出,應在我國刑事訴訟法“總則”中增設無罪推定原則。關于如何表述,一種觀點主張采納多數(shù)國際公約的規(guī)定,將這一原則表述為:“任何人未經(jīng)司法機關依照法定程序判定有罪以前,都應當假定為無罪的人。”另一種觀點則主張表述為:“任何人未經(jīng)司法機關依照法定程序判定有罪以前,都不應當視為罪犯。”還有個別學者和專家以無罪推定違背實事求是原則以及不符合中國國情為由,反對在刑事訴訟法中規(guī)定這一原則。
我們認為,盡管各國憲法、法律及聯(lián)合國有關法律文件對無罪推定原則的表述各不相同,但這一原則的基本內(nèi)涵和意義卻是舉世公認的。無罪推定不是對被告人作出的無罪判定或終結(jié)性結(jié)論,而是對他在刑事訴訟中所處地位的保護性假定;它要求控訴方以對被告人無罪這一推定作出反證的方式承擔證明其有罪的責任,并要求這種證明達到最高的證明程度;它要求被追訴者在訴訟過程中擁有一系列與指控方對抗所必須的程序保障。無罪推定原則為被追訴者充分行使訴訟權(quán)利奠定了堅定的法律基礎,并成為任何人受到無根據(jù)或不公正的定罪的重要障礙。正因為無罪推定原則在維護司法公正方面具有普遍的重要意義,修正后的我國刑事訴訟法結(jié)合我國國情吸收了這一原則的基本精神和要求:(1)明確規(guī)定“未經(jīng)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第12條),即明確被追訴者在判決前不是有罪的人。(2)要求控訴方承擔舉證責任:公訴人在法庭調(diào)查中有義務向法庭提出控訴證據(jù),如詢問證人、鑒定人、出示物證、宣讀書面證據(jù)材料等,以此來證實自己提出的指控主張。(3)規(guī)定被追訴者沒有證明自己無罪的義務,檢察機關和法院在證據(jù)不足,不能認定其有罪時,要作出無罪的處理。
三、我國的刑事訴訟法中無罪推定原則的特點
與國外通行的無罪推定相比較,我國的刑事訴訟法并沒有全盤照搬,而是根據(jù)我國的實際國情,結(jié)合我國刑事訴訟的實踐經(jīng)驗和需要,對其進行合理的取舍,因而具有以下特點:
1、我國的無罪推定原則更側(cè)重于實質(zhì),而不僅僅是稱謂問題。在立法上沒有使用“假定其無罪”和“不能被稱為罪犯”等表述,而是使用“不得確定有罪”的表述。
2、在證明責任的問題上,不僅強調(diào)了國家機關在形式上的責任,而且更加強調(diào)其實質(zhì)上的證明責任。在國家機關履行職責時,不是強調(diào)被告人的消極對抗,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均不享有沉默權(quán),而是強調(diào)控辯雙方的積極配合,當然,并沒有要求被告人承擔證明自己無罪的義務。
3、作為一項法律原則,明確規(guī)定了偵查、起訴和審判機關的行為標準,要求既注重結(jié)果又要注重過程。
四、對無罪推定原則的正確理解
刑訴法第12條將“未經(jīng)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規(guī)定為刑事訴訟制度的一條基本原則,有人據(jù)此認為我國新刑訴法采用了外國法通行的“無罪推定”原則,這種認識并不確切。首先,應該明確,外國法中的無罪推定原則包括被告人對被控罪行有權(quán)保持沉默,被告人在刑事訴訟各階段均享有充分的辯護權(quán),被告人沒有證明自己無罪的舉證責任,案件事實認定遵循“疑罪從無,疑罰從輕”原則等諸多內(nèi)容,我國新刑訴法對此并沒有全盤照搬,而是進行合理的取舍,確立了自己的特色。例如,根據(jù)新刑訴法第93條,第139條和第155條之規(guī)定,犯罪嫌疑人應當如實回答偵查人員的提問,被告人必須回答公訴人及審判人員的訊問,因而均不享有沉默權(quán)。新刑訴法確立的無罪推定原則的主要含義有兩條:第一,在刑事訴訟活動中人民法院依法獨立享有對被告人的最終定罪權(quán),具體體現(xiàn)在新刑訴法第12條的規(guī)定和取消了人民檢察院的免予起訴決定權(quán)。值得的注意的是,這里強調(diào)的是“最終定罪權(quán)”,無罪確定權(quán)仍由公安、檢察及法律規(guī)定的其它特定機關通過不立案、撤銷案件、不起訴等手段不同程度地依法行使。其中,對于相對不起訴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檢察機關在“不起訴決定書”中仍應確定“其行為已構(gòu)成犯罪”,因其符合新刑訴法第142條之規(guī)定,決定不予起訴。因此,檢察機關對部分案件不起訴決定權(quán)仍屬廣義的定罪權(quán)。第二,在人民法院依法確定被告人有罪之前,任何人不得將其作為有罪的人對待。此條為無罪推定原則的關鍵性內(nèi)容。受刑事追究的人,即使其犯罪事實已相當清楚,證據(jù)已足夠充分,即使其民憤極大,即使高層已有“明確”指示,但未經(jīng)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從法律上仍不能確定其有罪,因而不能將其作為有罪的人對待。這是樹立法律權(quán)威性的必然要求。任何凌駕于法律之上的主觀臆斷和感情用事都是極其危險的。
五、無罪推定原則確立的重大意義
我國最高權(quán)力機關以立法的形式確認無罪假定原則決非偶然,而是符合刑事訴訟的客觀規(guī)律和現(xiàn)代文明國家司法程序的實際需要,是我國民主與法制建設的重要里程碑,因而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確認無罪假定原則,有利于解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地位問題。在我國,由于過去的立法沒有無罪假定的規(guī)定,在司法實踐中,不少辦案人員的頭腦中總是抱有“嫌疑人、被告人進門三分罪”的錯誤觀念,因而難免先入為主和主觀臆斷,不能從根本上克服“左”的思想傾向和解決刑訊逼供等嚴重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權(quán)利的現(xiàn)象。現(xiàn)在以立法的形式確認無罪假定原則,就可以劃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與罪犯的界限,明確“涉嫌犯罪”與“判決有罪”的區(qū)別,從而自覺地以辯證明唯物主義認識論的理論為指導,切實克服先入為主和主觀臆斷的錯誤傾向和做法,有效地保障人權(quán)。
其次,確認無罪假定原則,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以辯護權(quán)為核心的訴訟權(quán)利,充分發(fā)揮辯護制度的作用。在封建專制時期,刑事訴訟奉行“有罪推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是刑事訴訟法律關系主體,只是受拷問被追究的對象,無任何訴訟權(quán)利可言。當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勝利并確立無罪假定原則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才成為刑事訴訟法律關系主體,在法庭審理過程中,被告人才擁有與原告對等的訴訟地位,享有以辯護權(quán)為核心內(nèi)容的各項訴訟權(quán)利。如果我們不能旗幟鮮明地確立和承認無罪假定原則,即使法律明文規(guī)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辯護權(quán),但在司法實踐中往往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和保障,形同虛設。這已是被歷史證明了的而毋庸置疑的客觀事實。
第三,有利于進一步明確證明責任的合理分配和疑難案件的正確解決。無罪假定原則的重要內(nèi)容之一就是證明責任由控訴方承擔。控訴方指控被告人犯罪,必須提供相應的證據(jù)事實加以證明,而且這種證明必須達到法律規(guī)定的標準,即犯罪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如果控方不能證明被告人有罪,被告人就是無罪,被羈押的被告人就要無罪釋放,并按照國家賠償法賠償損失,恢復名譽。在司法實踐中,有時由于各種主、客觀原因,有些案件不可能查得水落石出或者一時難以查清。對于這些證據(jù)不足、“處斷難明”的疑罪案件,在實行有罪推定的封建專制訴訟中,一般是按照“疑罪從有”或者“疑罪從輕、從贖”來處理的。這充分說明封建訴訟的專橫擅斷和對人權(quán)的踐踏。但無罪假定即要求司法機關的司法人員對疑難案件的處理不是從有、從輕或者從贖,也不是從掛,而是應當從有利于嫌疑人、被告人的角度來解釋和處理的。即: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無罪一時難以確定的,按無罪處理;被告人罪重、罪輕一時難以確定的,按輕罪處理。
第四,有利于在國際人權(quán)斗爭中爭取主動權(quán)。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歷來倡導在刑事訴訟中必須認真貫徹“以事實為根據(jù),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對被告人定罪判刑必須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這樣的訴訟要求和證明標準本來高于西方國家所謂的“排除合理懷疑”和國際上的其它標準,然而,在過去的立法上卻諱言“無罪假定”,豈不是“作繭自縛”,授人以把柄,使我國在國際人權(quán)斗爭中陷于被動。同時,如前所述,聯(lián)合國一些重要的人權(quán)文獻和國際公約都規(guī)定了無罪假定原則,其中有些是我國參加、締結(jié)或明確表示贊成的,如果我國刑事訴訟法不確定無罪假定原則,這同我國是聯(lián)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國際地位是不相稱的,也難以自圓其說。所以,新刑事訴訟法確認無罪假定原則,不僅有利于在國際人權(quán)斗爭中爭取主動權(quán),也是對外開放以及同國際接軌的實際需要。